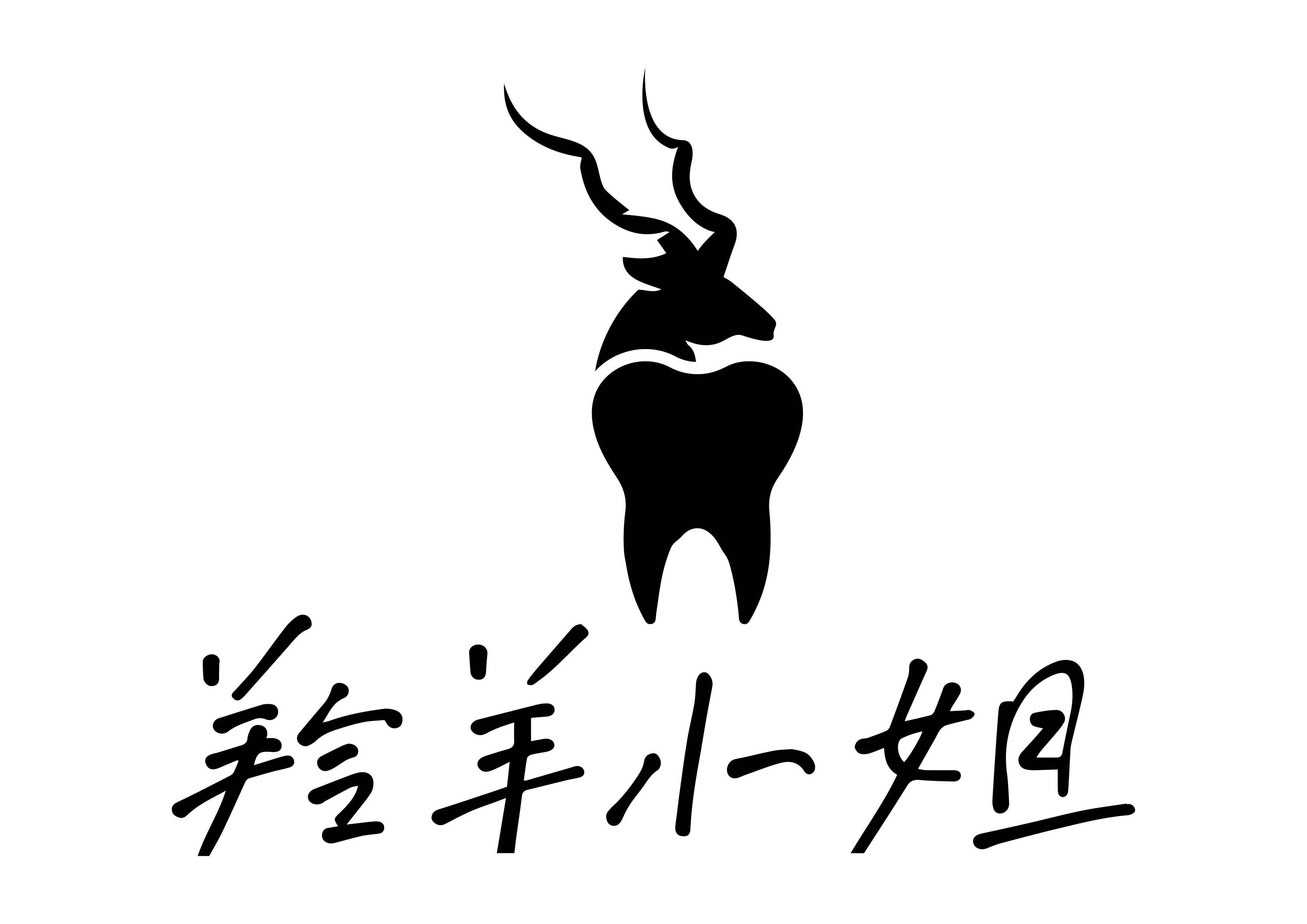那時候只覺得奇怪,住在走廊最尾端1C的和藹伯伯,對我們總是有說有笑的
怎麼開個刀出來,開始胡言亂語,甚至拳打腳踢到需要上約束帶
後來到了成大才知道這就叫delirium
阿宏學長會有幾個定番的問句,都是拿來測試人事時地的定向感(orientation)
- 你叫什麼名字
- 你在哪裡
- 現在是白天還是晚上
delirium這種意識障礙,卻會讓病人反反覆覆
彷彿清醒有時糊塗,有時會陷入精神蟲洞中
自己已經走了很遠很遠
陳永天(名字經過變聲處理XD)是個江湖氣很重的紳士
之前補過的free flap在他臉上都像淬了風霜的劍傷,但是不是道上人士我就無從得知了
在全麻刀上消毒的時候
可以瞥見他背後細膩的刺青
是一條老派卻炯炯有神的龍
簽同意書的字體堪比國文老師的板書
一撇一捺甚至更為大氣不拘
我去解釋手術以及開刀風險的時候,他也是腰桿挺直,像後面綁了個脊椎支架一樣的點頭抄筆記,筆記旁擺了他一直在抄寫的心經
但開完刀之後,他不可避免的還是混換躁動了起來
阿宏學長晚上去查房的時候,也是把定番的問題拿出來問
這麼一來一往幾次的某天早晨
“你在哪裡?”
因為術後還插著氣管的緣故,我們都是用筆談的方式進行
但見永天爺爺遲遲不動筆,學長繼續追問,“我們是在你家嗎?”
搖頭。
“我們在長照機構嗎?”
搖頭。
“我們是不是在醫院?”
點頭。
“這裡是哪裡?”
爺爺寫下鋒利的二字:成大。
“你叫什麼名字?”
這時候我們從爺爺一如繼往嚴肅冷淡的撲克臉中,感受到他若有似無的怒氣
只見他寫下
永天大爺
學長在他寫出永天二字之後,似鬆了一口氣般、恍若沒看到大爺二字的繼續追問,“現在是白天還是晚上?”
“ㄆㄧㄚˋ”的一聲,永天爺爺用力把筆摔在板子上,好像那是把上了膛的槍
然後用盡全力而顫抖的手指指向窗外的明亮天光。
給阿宏學長嚇了好大一跳,“爺爺不要生氣,我們不是在戲弄你啦,我們只是想確認一下你的精神狀態,有沒有睡好這樣。”
雖然因為皮瓣手術補的範圍很大,永天爺爺後來還反覆去了整形外科,清創沒有長好的肉跟壞死的組織
但在一個雲淡風輕的下午,他就默默的從整外那邊出院了
後來在6A的醫師休息室裡看到一張日曆紙,後面是俐落的鋼筆字體,“謝謝大家的照顧。”
我一眼就認出那字跡,每次在旁邊key note的時候都要克制自己想把薄薄的紙帶回家的衝動。
有時候真的不能怪病人不好好刷牙,在口外的第二週的午餐時間,我接到了一個切片

一邊有定時炸彈 
沒有的另一邊也是淒淒慘慘戚戚
病患是退休教授,帶著斯文板正的金邊眼鏡,是我男神過去的頂頭上司
太太總是陪他一起來,一邊碎念他不可以懶得走路,一邊叮囑他小心地上

但帕金森氏症讓他oral hygiene注定差勁,重聽還有輕微的理解障礙都在我們之間隔了一層毛玻璃
第一次切完片收集資料、拍拍照,倒是還好
但到了第二回,口腔衛教、解釋病理報告、說明治療計劃,都是複雜繁瑣的工事
一開始我還嘗試想要向伯伯解釋,但吼到後來,自己也有些疲倦
隱約察覺他其實不是那麼理解,我便轉頭向他太太繼續說明,
“回去之後可以幫他像這樣拿著牙刷….”
教授持續用顫抖的手指,輕敲著輪椅的扶手
但失焦的雙眼透露著他並沒有跟上我們的對話
下一回來的時候,我們重新上了牙菌斑顯示劑
查看了傷口癒合情況跟牙周清潔狀況
出乎我意料的,口腔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,也是我第一個刮完follow到的人

“他回去刷的可認真了!”,太太一來就對我說
只見老教授賣力地握緊牙刷,在口內向我筆畫,“這 — 裡 — 這 — 樣 — 嗎 — ”
那個剎那,愧疚感跟羞愧的情緒一下子漲潮了起來
醫者要的同理心、溝通力,我一個都沒能做到
想到上回的永天大爺,阿宏學長就算在他delirium的時候,也是盡力地問她睡得好嗎?有沒有其他狀況?再兩天就可以拔掉鼻胃管囉
不曾因為雞同鴨講的尷尬,就略過他,轉而向親屬或是看護說明
就像我們在兒牙,tell show do對的是小病人而不是他爸媽
在那之後的幾次
老教授拿出他的老式手機,說要加line
老太太在旁邊笑,說他老是忘記自己那是3310 是智障型手機
倒是老太太跟我交換了聯絡方式,寒流的時候清晨會傳訊息來說今天10度要我多穿點
療程結束的那個禮拜,讓人運了一箱椒井水到我宿舍來,說女孩子喝這個好

我想著,何得何能。
遇到一對可愛的老年夫婦,偶而鬥嘴,但平淡長久、千帆過盡也不離不棄
比豔遇繁華更不易
就像電影裡這兩位
謝謝口外病人教會我的。
(後記:最後一次看診我居然還能像他請教有限元素分析法了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