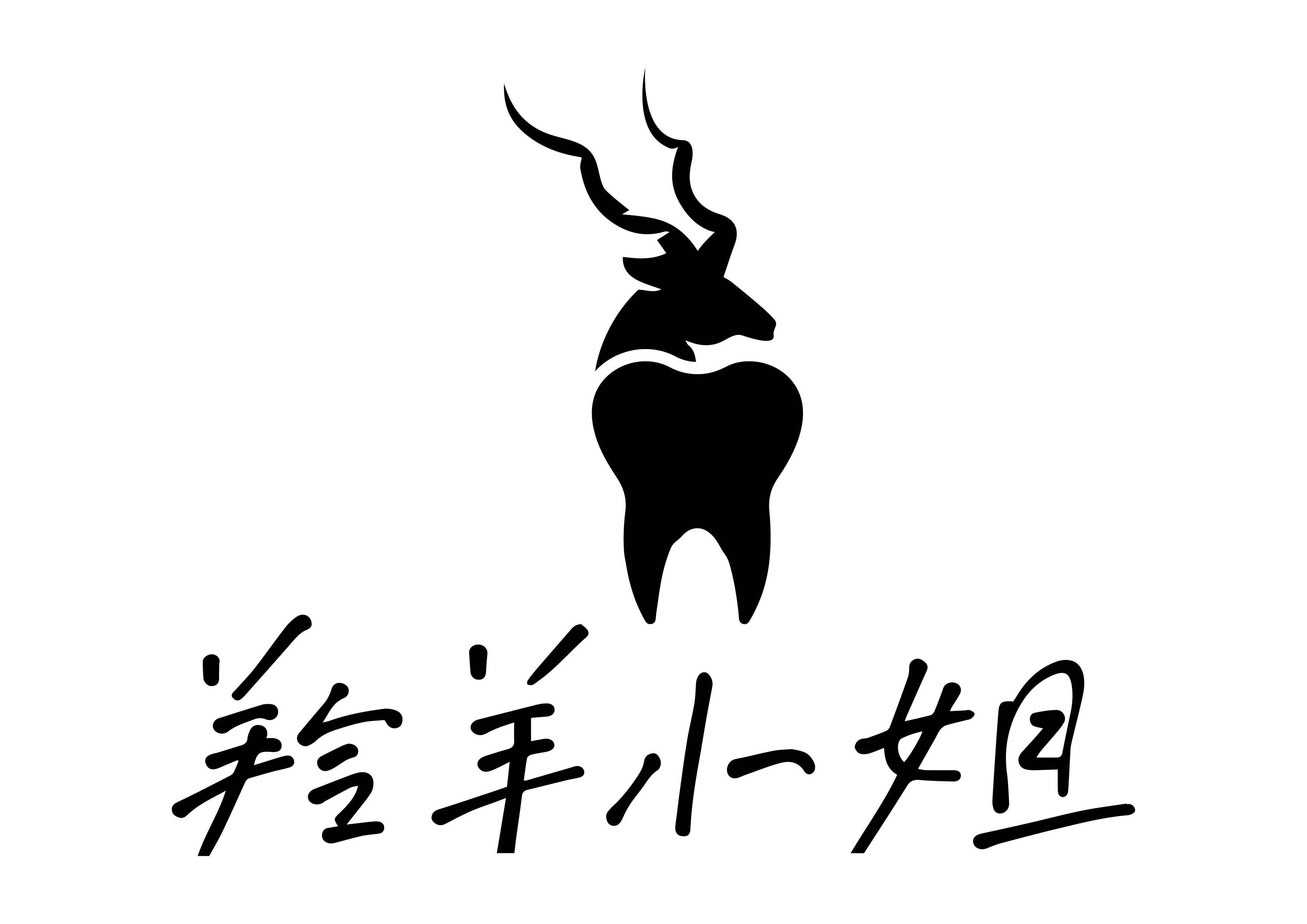會面是離別的開始,再見就是人生的全部。
— — 《人間失格》 太宰治

真人真事,沒有改編。
沒有穿鑿附會,強解人意,文中的”我朋友”,沒錯就是我XD
至於文中的”我”,親愛的ㄞ,新年快樂。
凌晨的海上停著大片大片的積雨雲,冬天總是這樣,要下不下的
“你知道消失是什麼樣子的嗎?”
“什麼什麼樣子的”浪聲很規律,你的聲音低低的,拍打在岩石上。
“一滴水掉進大海,就消失了耶。”
你瞥過頭來看著我,“嗯哼?”
“不覺得很悲傷嗎?”
“哪裡?”
“沒事。”我撿起一顆小石礫,用力地拋進海裡,突然的歇斯底里。
那滴水就消失了耶,大海裡一直有他,大海裡都是他,卻再也找不著他了。
三年後再次遇到你,沒有什麼時間靜止、沒有倉皇失措,也沒有近鄉情怯的閃躲迴避
好像那些浮誇的情感全給了夏天夜晚裡的舟山路了
以至於我們完全能成熟而友好的寒暄
我可以再次直視你閃閃發亮的眼睛,上下滾動的喉結,甚至是不經意的酒窩
而不深陷其中
那個夠格談失去的瞬間,我為自己感到驕傲。
但悲傷的是,我仍記得種種難忘回不去的細節
那個關於你的一切都鑲了金邊的下午
在你之前,我也喜歡過其他人,交往過別的什麼人; 在你之後….
我不是一個相信那些閃閃發光定義的人
一見鐘情、命中注定、天生一對、非你不可、“Moment”….
那些對我而言都是好遙遠好遙遠像在另外一個星系的詞彙,眼見才能為憑,就算光要走好遠好遠。
所以我有自己的checking list:
要高,至少要比我高
笑起來要溫柔,就算沒有酒窩
要有安全感,長相除外。
啊,不可以有不良嗜好
第一次見你,在椰林大道上,你逆著光騎向我
像從很遠的星系,穿過蟲洞而來,夾克鼓鼓的,塞著飽滿的風
眼見為憑。
那個Moment我想我不可能再喜歡上別的什麼人了
只有你,只能是你。
你跳下腳踏車,大步走向我
“啊,來不及了。”,我想
你沒有比我高,襯衣的口袋裡還明顯鼓著菸盒的形狀,笑起來很陽光卻也很粗獷,露出一口整齊的白牙
可是來不及了
那是一見鐘情。


台大溫州街一帶很多違章建築,美是美,大夥說起,卻都是“影響市容”、“治安死角”
我猜想你是否對我不合時宜的愛戀了然於心
所以國才出的這樣無聲無息
我的老朋友在台中當起了牙醫,我們一起分食一塊舒芙蕾的時候她突然端詳起了我的虎牙
“等等來我們診間看一下。”
“怎麼了,這麼突然?”
“你犬齒吃冷吃熱會不會不舒服?”
“是有一點,到底怎麼了你搞得我好緊張。”
搭客運前我們刻意經過了台中榮總
她收起一堆尖銳的器械,拿下口罩後難得嚴肅的說,“不行,你這顆牙齒神經要抽掉了。”
“為什麼?”
“就有蛀牙你又沒去管它,細菌越跑越深,把你的牙髓細胞慢慢吃掉了。”她一邊打病歷一邊回頭對我說。
“可是之前我有補過牙齒耶”
“嗯嗯這也有可能,補完之後下面又再蛀。”她一臉無奈。
等等,這不對吧,無奈的應該是我吧。
這種徒勞無功的感覺令人沮喪,明明都填補起來了,明明我們彼此都盡了全力,細菌入侵後好像就賴著我不走了,好像我終其一生都沒有痊癒的權利了。
“那抽神經會痛嗎?”
“會啊,怎麼可能不會,你細胞又沒死全。”
“那要等他死透嗎?”
她呵呵地笑了,停下打病歷的手,笑容看起來有點陰險:“我們不用等他死全也能把細胞全部挖出來,然後再填進一些緻密的人工物。”
“聽起來就好恐怖。”
“會怕就好。”她脫下手套總結。
她不知道,我已經把自己全部挖出來了,可是什麼也不想填回去。
“睡了嗎?”
棉被旁的手機螢幕微弱的亮起,一明就滅像夜晚裡的女宿一樓販賣機
“帶妳去兜風”
自行車在舟山路穿梭着,我偷偷的把冰可樂貼在自己的把臉頰上,夏晚太熱
風迎面而來,你襯衫後背都因爲炎熱而洇濕。
昏黃的街燈時有時無,想必長久以來這個城市也不是很在意這個時間點是否有光
畢竟這時刻會在外頭晃悠的人們,都心照不宣的偷偷期待路燈再少一些
一到路口,你會停下來扭過頭,湊過來喝一口我手裡的可樂,淺淺的打了一聲輕嗝,然後再轉過身繼續賣力騎車
夜晚涼涼的貼在我們的背上
那真是電影原聲帶轟轟烈烈從天而降的時刻

躁動懵懂的青春時期,就像是在坡路上撒開車把肆意前行。
每每回想起這個時刻,我都像宿醉後強迫自己清醒上班的早晨,似要耗盡我畢生的氣力
再見到你,跟初見有一樣的風
“你….”
“我回來了”,我以為他們有告訴你
沒有的,所有人都知道你的消息,除了我。
回家後我情不自禁的打開對話框,最後一句話停在“你什麼時候回台灣?”
明明音訊全無,明明面容改變,卻還是該死的白襯衫尼古丁、該死的夾克舟山路
隔天我起了個大早,自己坐了好久的公車去海邊看海
一滴水掉進大海,再也找不著了,卻稀釋了整片汪洋。